杨齐心:腊味飘香忆旧年 | 天眼新闻文化频道·春节记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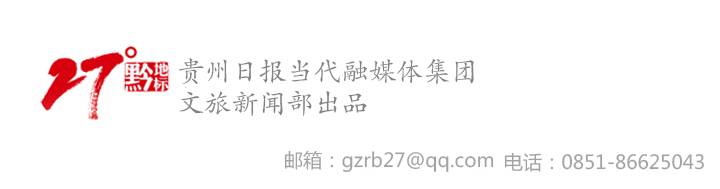

当贵州高原的年味氤氲在腊月的空气中时,我总会产生一种思绪,这已然成了一种习惯。这思绪强烈地萦绕和荡漾在心间,像一坛老酒,那醇香总使我忍不住揭开坛盖,呷上几口,体味那逝去岁月中的甜美与幸福。
我的老家久长是贵州修文的一个小镇,童年那会儿只有三四百户人家。每到过年的时间,那里总是下雪。在雪花纷飞中,在几棵光秃秃的高大的杨槐树下,几个在斜坡上戴着瓜皮帽呼着热气来回游动的小黑点,那是过年无事尽情滑雪的我们。这时的小镇在白茫茫中许多人家升起青青的柴火烟,那烟缓缓地飘向灰蓝的天空中,让小镇显得无比静美。最快乐是出太阳的时候,没有风,干冷干冷的。阳光照在雪上,到处闪闪的。高高的杨槐树上几只喜鹊按耐不住兴奋,喳喳地在树顶丫枝上扑打着,弄些雪粉飘下来,掉在背心里冰冰的、凉凉的。茅草屋檐上,一米多长的冰挂开始融化,有的啪啪的掉下来,摔成几截。于是三五个孩子捏上雪团,在飘着腊肉香的农家间,在马路上,你追我打,露出脚趾的布鞋湿透了也全然不顾。渐渐的越聚越多,大小伙们也加入,雪团飞舞处,成了小镇最热闹的地方。这样的时候,父母是不会管的,他们都在张罗着过年的事。但有一件事他们总拉我们帮忙做,那就是舂粉子面(糯米面)来包汤圆。
我们舂粉子面用的是碓。那时我家附近只有一户姓童的人家有碓。这碓实际就是一个宽十五六厘米,深20多厘米的一个石窝(我们叫它碓窝),舂碓的碓杆是一根一米五左右长的粗圆木,碓杆在碓窝的这一头用稍细一点的木柱装成啄头,碓杆的另一边削平供舂碓的人踩踏。削平处的前面穿一圆木,圆木的两端分别插入两块直立的扁石中作支撑。整个碓的设计就像鸟往石窝里啄食一样。舂碓的人用力踩在碓杆的扁平处,碓杆另一端的啄头就跷起来,脚一松,啄头就啄下去。在一踩一放中,碓窝里的糯米就被捣碎了。我们舂面的时候,母亲就蹲在碓窝边,将窝中的糯米面舀起来放在细孔筛里筛,完了又将粗糙的倒入碓窝中继续舂。我们小孩是最耐不住性子的,一上去就使劲舂,希望一下子把它舂完后好去玩。哪知力气用尽了才舂得一小点。这时母亲总会笑着说:“娃儿,心急吃不得热稀饭,慢工才会出细活。”于是在急迫中,在无奈中,便硬着头皮舂上三五小时方完事。也就是在那时悟出了一个道理——做什么事得有耐心,有些事一下子是做不好的。人家多碓又少,点上煤油灯雪夜舂碓的事也是常有的。“咚嗒”“咚嗒”“咚嗒”……那腊月的舂碓声,成了记忆抹不去的回声。
在腊月里,最有趣的莫过于吃霉豆腐。那时,霉豆腐是高原小镇每家过年必备的一种食品。经过选豆、泡豆、磨豆、煮浆、吊浆、点浆、压榨成型等一道道工序后,便做成了一块块的白豆腐。再将这一块块的白豆腐切成二三厘米方正的小块存放,长霉后取出,裹附上花椒、八角、山柰、砂仁和盐等混成的香料装坛。几天后开坛,那股喷坛而出的臭味和浓香,让人禁不住口水直流。在吃饭的时候母亲就会用筷夹出两三块放在盘子里盛上让我们品尝。边吃边叮嘱我们说:“少吃点,吃多了会变憨的。”为了不变憨,我尝几下就不敢再吃了。那味道又挡不住,冒着变憨的危险又继续吃。年龄稍大后反思,那又臭又香的东西太少了,一年才做一小坛,如果不节约吃,很快就会被吃光,母亲是用变憨来吓唬我们的,好多吃几顿。
除了吃霉豆腐,腊月还有一件更有趣的事让我着迷——那就是烤腊肉吃。
冬至过后,辛苦了一年的小镇人家几乎都要杀年猪,这是庆年的一件大事。大人小孩喜气洋洋,烧水、抓猪、开膛破肚、分割、吃刨汤,一切都有序进行。完事后余下的就是熏腊肉了。熏肉的柴是家门前青龙山上砍来的青冈柴,要么是虎山和后山猫冲刨来的松树疙兜(树桩),当然柏树枝熏来最好,熏的肉红香味美,不过柏树枝是很少的。当成块的肉经过用盐腌上两三天后就在灶房里上架挂熏了。点上火,满屋烟拂过后,白色的肉开始渐渐地变色,浅黄变深黄变浓黑。水滴与油的混合体常常掉在火上哧哧地燃烧,升起一团团火焰。夜晚时,全家人围在柴火堆旁,看着红红的火、闻着弥漫着的腊肉香,开心着。而屋外,槐树枝被冰凌压断的咔嚓声和寒风吹雪的呼呼声,让灶房里显得无比的宁静与温暖。
这时,父亲总会做一件事情,将腊肉切下一大块分成几片,用铁签穿上,放在柴火上烤,冲鼻的焦味和肉香马上充满了整个屋子,我忍不住伸手想撕。肉烤好后,父亲就一块块的取下分给我们兄妹,将最小的留给母亲和自己。我们接过烤肉,一丝一丝地撕下放入嘴中,慢慢地嚼着很久也舍不得吞下。在那吃饭都有困难、吃肉得等过年的年代,在雪夜吃上那样的烤肉,那是何等的人间美味呀!
而今,父母已不在世,我也离开小镇七八年了,每到过年,总会想起小镇过年的许多趣事。那纯真年代腊月的炊烟,腊月的肉香,腊月的繁忙,却总是让我回味。
文/杨齐心
刊头制作/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实习生 杨简
文字编辑/李缨
视觉编辑/赵相康
编审/李缨
